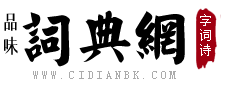德经·第六十七章
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。知者不博,博者不知。善者不哆,哆者不善。
圣人无积。既以为人,己愈有;既以予人,己愈多。
故天之道,利而不害;人之道,为而弗争。
〔注释〕
乙本作“善者不多,多者不善”,甲本缺数字。兹假定“多”乃“哆”之省写。通行本作“善者不辩,辩者不善”。义同似。哆,张口大言也。
能行本末二句作“圣人之道,为而不争”。兹据甲、乙两本。“天之道”与“人之道”对文。
〖臆解〗
“信言”,今语曰“真话”。──六经中无“真”字。老子中有之。如:“其精甚真”、“质真如渝”,皆形况词,与“信”(读如“伸”)通用。如“其中有信”,今语曰“其中有真理”,则形况词之为名词者。
欧西自寇桑(Victor Cousin)申“真、美、善”之说,尔后哲学界无异辞,皆以为人生之向往与归趋,无以非难。三者,古代各民族多有说,希腊为著。在东亚,则老子此章是也。各有所重。于此章又出“知”与“博”相对为言。当属知识论。倘视三者为三元体,如三圆球,各不相涵,以谓真者不必美,美者不必善,则说人生现实亦大致不诬,悲剧皆由此起。然此盖然之说也。论于理实,亦难谓真者必不美,美者必不善。或三或二,亦可有相互涵摄之时。老氏之历史哲学,所见者如此,非如近世之纯思辨哲学,未为经验论所范围者,所见不同。
虽然,老氏此说,盖为其著书而言。故后人编此为其书之末章。信与伪,美与丑,善与恶,可为相对,老氏亦必不以信与美,以美与善为相对。第申其旨,若曰:如此书者,不美、不博、不哆,然为信、为智、为善。进而言“圣人无积”,则仍申其著书之旨,如是而为教,教人之为人也。
且“圣人”,依老氏之义,为侯王而明圣者。则其积,货财也,非无所积,乃积于民。所谓“公忠体国”,与其国为一体者也。己之所有,即国之所有,即皆民之所有也。岂非“既以为人,己愈有;既以予人,己愈多”乎?
倘使侯王而有私积,如唐之琼林、大库者。是聚敛之臣,搜括于民间,则或储存而腐朽于无用之地,或备逃亡之资而已,或肆寇盗之钞掠,或供子孙之暴殄奢糜,且贻祸于国家,此史之大戒也。侯王之冀为圣君明主者,必不然矣。──此现实之义也。
或者,“圣人”非谓在位者,则体道者也。道无可积而德可积,学可积。将谓“圣人”无积德、无积学乎?曰积学积德,皆为道也。为道非徒为己也,亦为人也。既以予人,己且愈多也。愈以为人,愈以予人,则德愈积而道愈富,亦自然之理也。──此抽象而言之也。
基督尝有是言:“有者,将予之;无有者,并其所有而将夺之。”是也。同此理也。谓有者,有道者也。无有者,无道者也。有道者,增其明;无道者,去其惑。
“天之道”,昭明之理也。理有非人所能知,盖自然之道也。为生为杀,为利为害,多非人力可为。人类至今仅能作少分“先天而天弗违”之事,未能征服自然也。然人类实进化者。自然而生人,亦无必生之以害之之理。故曰“利而不害”。“人之道”,既为人、既予人矣,则亦无争。故曰“为而弗争”。